

《中华读书报》继12月14日头版头条刊发《名师大家学术文库》书讯——《赓续西北大学学脉11位学术大家代表作被抢救出版》后,12月21日在“文化周刊·国学”版,整版对其中张西堂、陈直、刘持生、李仪祉四位先生及其学术思想作出评介。
随着时代的潮涌,他们的名字正渐渐被淡忘。西北大学出版社历时五年精心编纂的《名师大家学术文库》(第一批)堪为从落满尘埃的“故纸堆”中发掘出来的内容,有的经由健在者修订,有的由专人整理,有的由后任学术继承人校核梳理,此举颇具抢救性意味。本版特约一组文章,让我们在那些领受过先生们真传的学者的述往里,得见这些有着慧心灼见的大先生们渐行渐远的背影。西北大学的这些“夫子”们,或风流儒雅,或严谨持重,或述而不作,或刚强自持,都表现了中国文人自古最为看重的风骨。
经学家”张西堂先生
文|田旭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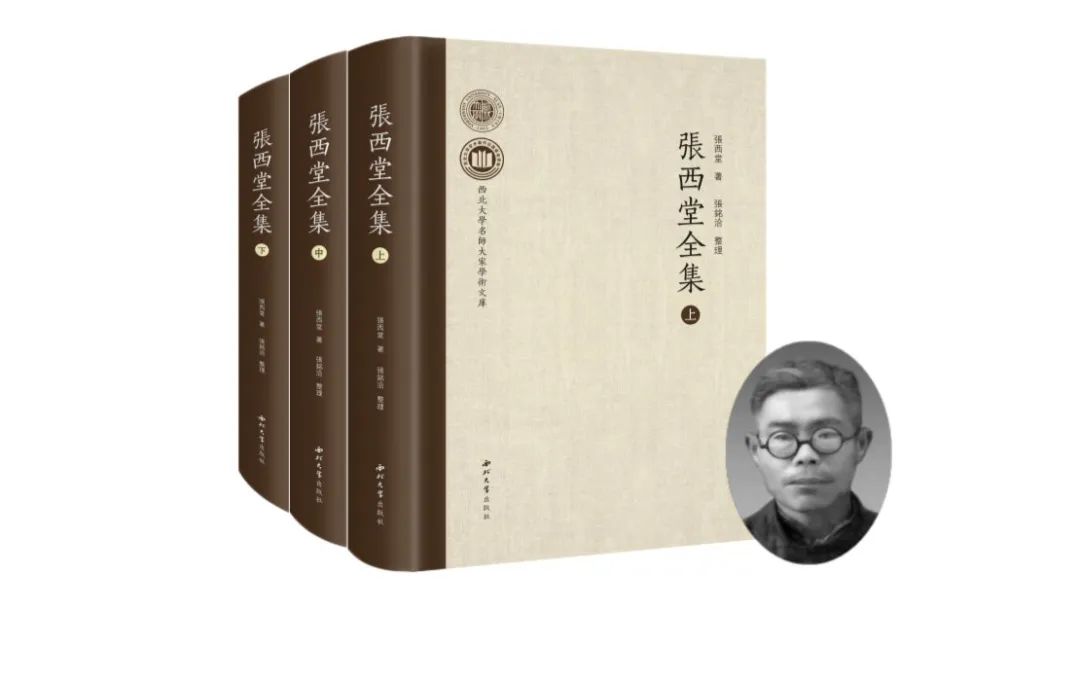
《张西堂全集》共收了20多部著作,洋洋370多万字,涉及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学与诸子百家之学,充分显示了张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与先生多年来为学术研究呕心沥血的学术精神,每一部都是博大精深的学术巨著。
作为一名后学,本人仰慕先生的学术成就,亦为不能全面理解先生的学术贡献而诚惶诚恐,仅在这里谈两点自己粗浅的体会。
先谈谈被誉为经学家的张西堂先生对经学研究的贡献。先生5部著作(《经学史纲》《经学概论讲义》《诗经六论》《尚书引论》《谷梁真伪考》)和24篇论文集中于经学研究,涉及了全部六经,尤其偏重《诗经》《尚书》及《春秋》。
对传统学术经学和诸子学研究的意义,尤其是经学研究,从西汉孔壁出书引发的经今古文之争,延宕了两千年,初期经传文本及文字诠释的异同、是非、真伪之辨,渐次扩大到两派的学术路线、思想倾向及学风、方法之争,更涉及到传统文化及学术史观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古史的疑信问题、孔子的地位问题、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等,足见其深远与广阔的影响。
关于经学历史,以往我们所熟悉的只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和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皮锡瑞是以今文经学的视角来叙述经学史的,没有摆脱今文经学的束缚。马宗霍从学术史立场撰写的《中国经学史》,更是中国第一部经学通史,彻底改变了中国经学史研究落后的局面。
张先生的《经学史纲》全面系统深入详尽地总结了经学的发展历史和相关问题,然而仅叙述到东汉,对之后经学所历经的魏晋隋唐至清末的研究状况并未涉及。之前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正式出版,最终由其子嗣张铭洽完成了艰难的整理工作而出版,为经学研究增添了一部力作,从学术史角度看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说说张西堂先生在古史辨运动中的贡献。在二十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一股对中国传统的古史观进行怀疑和批判的思潮在中国史学界兴起,这就是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为代表的疑古学派或古史辨学派,他们以《古史辨》为阵地,对传统的古史系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砍伐,使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传统的古史系统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当时,这一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史学界,并在以后影响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
从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到1941年的15年间,《古史辨》出版了七大册,共收录学术论文350余篇,当时学界著名的学者几乎都著述立说,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研究和探讨。作为治经学与诸子学的著名学者,张西堂先生在30年代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他先后写有5篇文章分别刊登在《古史辨》第四、第五、第六册中。
《古史辨》第四册是由罗根泽先生编辑的《诸子丛考》,专门考辨诸子问题,其中刊登张西堂先生两篇文章,一是《陆贾新语考证》,一是《尸子考证》。《陆贾新语考证》对陆贾的《新语》引《谷梁》提出疑问,怀疑《新语》为真传。《尸子考证》对流传至今的《尸子》辑本进行考证,认为其大有可疑之处,认为《尸子》辑本亦不可信。
《古史辨》第六册是罗根泽先生编辑的《诸子丛考》续编,其中收有张西堂先生两篇文章,一是张先生应罗先生之约为这一册所作的《序》;一篇则是张先生考辨《荀子》的文章,题为《荀子劝学篇冤词》。在《序》中,张西堂先生就该册中所收有关考证《老子》的文章,特别提出重视证据的问题,他认为应从“思想线索”“文字文体”“时代术语”诸方面尽量地检查证据,实事求是地去做,即可早日解决《老子》的年代问题。另外,因发表在本册中的孙次舟《再评古史辨第四册》正好论及《尸子》和《新语》,张西堂先生又以较大篇幅对其进行辩证。《荀子劝学篇冤词》则对《荀子》现存32篇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其分为6组,认为《劝学》等14篇为荀子所作,但其中也间或有他篇错入者,具体对《天问》《劝学》等篇与他书之关系进行了比较和考证。
《古史辨》第五册中刊登的张先生之文《左氏春秋考证序》,是一篇较长的文字,也是最能体现张先生疑古观点的文章。
《左氏春秋考证》乃清代末年学者刘逢禄的一部大作。刘逢禄为清代今文经学派人物,他怀疑古文经,作《左氏春秋考证》,提出《左传》为刘歆伪作,率先对《左传》予以否定,受到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拥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即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左传》大加否定。梁启超亦对刘逢禄称赞道:“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
张先生的这篇《序》实际上是对《左传》的进一步考证。全文从5个方面论述,在肯定刘逢禄的同时又谈论到刘的不彻底之处,进一步肯定了康有为的观点,认为《左传》为伪是经过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崔适的《史记探源》才最终成为定论。文中还对章太炎反驳刘逢禄的意见一一进行了再反驳,认为章太炎是极端的信古主义者。最后,张西堂先生提出研究《左传》应当从两个方面予以注意,一是《左传》与《国语》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左传》与史料的关系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张西堂先生在古史辨运动中主要参与了对经书中的《左传》与诸子中《老子》《荀子》《尸子》及陆贾《新语》的考辨,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力对上述文献进行了更加周密的考证,在学术观点上基本继承了自晚清以来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人主张怀疑的传统,并对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在整个疑古思潮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古史辨学派自有它的学术贡献,如打破了古代是黄金时代的观念,反传统具有革命成分,其学术贡献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贡献;对古代文献重新审查,这无疑对学术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对传统古史观来了一个大扫荡,从而为建立新的古史观开辟了道路。张西堂先生亦在其中,与当时的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先生一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然,客观地说,张先生的学术研究受时代所限,一是过世太早,二是他没能看到后来有大量新材料的出现,特别是出土文物对史实的揭示和释证,因此他的研究颇为遗憾地主要是从文献到文献。
(田旭东,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弄瓦翁”陈直先生
文|周天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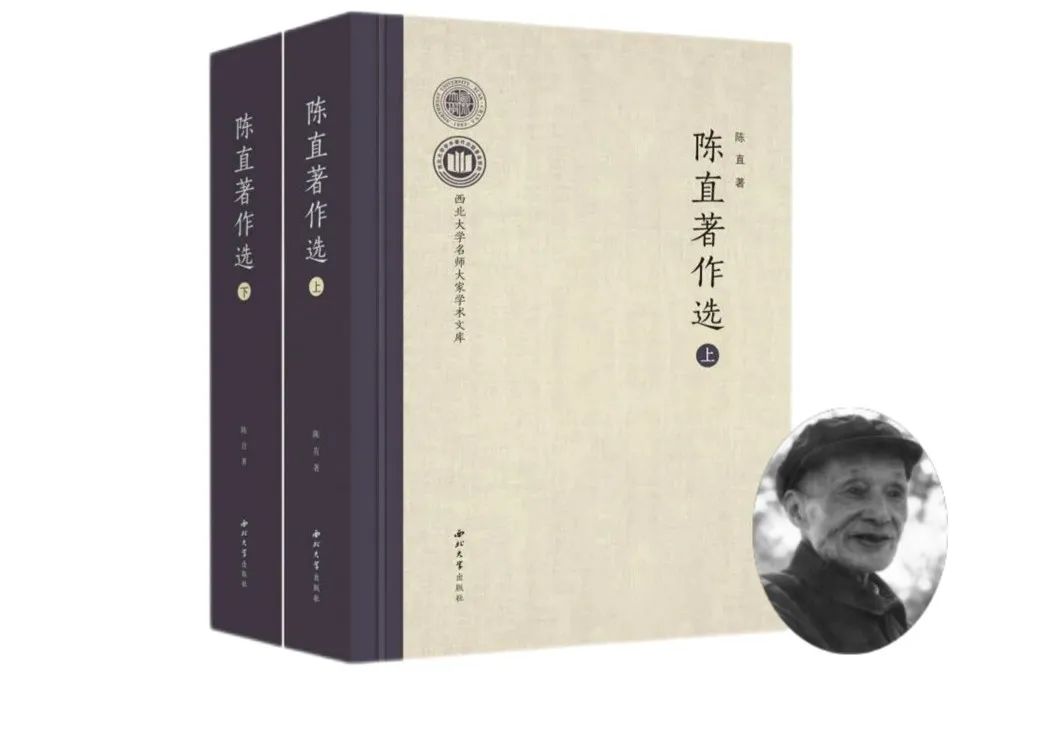
陈直(1901—1980),原名陈邦直,字进宧,又作进宜,号摹庐,又号弄瓦翁,江苏镇江人。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陈先生出生于清末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人家。祖父陈桂琛擅长诗赋,兼通医术,所以靠医糊口,并课徒养家。父亲陈培寿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过举人,但不热衷功名,依然设馆授徒,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陈家治学严谨,一直以古文字学为专精,兼及文史。比如陈先生整理发表的《古籍述闻》一文,便出自其父培寿先生之手。在家学的熏陶下,陈先生奠定了坚实的国学根基。然而与其嫡兄陈邦福、从兄陈邦怀一生致力于古文字学不同,他从十一岁开始转攻秦汉史。先是点读《史记》,继而通读《汉书》,以后每二年必通读一过,终身不辍。二十四岁时,便撰写《史汉问答》二卷,崭露头角。
陈直先生兄弟三人追随时代学术风尚,在关注文献之余,醉心金石之学。《摹庐诗约》中有一首诗写道:“我年十四五,喜摹金石字。我家三兄弟,采摭有同嗜。各各出所藏,一一相较次。”又说:“乾嘉诸老辈,攻金石刻辞。吾家数昆季,亦颇斟酌之。言笑有所获,传观乐不支。”不仅如此,他还与时贤黄宾虹、邹适庐、徐积余、周梦坡等过从甚密,不断交换关于古器物的研究资料和心得,于是又奠定了古器物学的深厚功底。在他四十岁前,就已发表了《汉晋木简考略》《汉封泥考略》《列国印制》《摹庐金石录》等著作,同时还协助丁福保编纂《古钱大辞典》。不难看出,陈先生把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结合起来,开展秦汉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竟与王国维先生创建的“二重证据法”不谋而合。于是他在秦汉史领域里纵横驰骋,游刃有余。
陈先生以自学成才闻名于世。经马叙伦介绍初到西北大学时,有人就嘲笑他没有学历,不懂外语,便在职称评定上一再卡他。殊不知陈先生在民国早期一度考取清华研究院,拟拜师王国维先生,不幸因家境困顿,学费无着,而不得不忍痛放弃这一求学良机,转而继续拜师访友,坚持自学。由于他对于国故的执着,引导他自觉继承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并首次引入秦汉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成为当代秦汉史研究的一面旗帜。所以,他一直以王国维先生的私淑弟子自居。
我曾在《关中秦汉陶录》一书前言上,总结了陈先生的四大学术贡献:第一,《汉书》研究。他在撰写《汉书新证》时,主张“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即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汉书新证·自序》),从而在前人耕耘过千万遍的“熟地”上,开拓出一条新路径,为后来的研习者指明了方向。第二,在秦汉经济史(主要是产业史)和相关的人民史方面,《两汉经济史论丛》的问世,粉碎了所谓秦汉手工业几乎无话可说,东汉尤其是一个空白点的断言,以文物证史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第三,汉代简牍研究。他持续时间较长,用力较勤,却大器晚成,自成体系。第四,有关瓦当陶文及封泥玺印研究。他弥补了文献的不足与缺失,可谓出奇制胜,居功至伟。
值得一提的是,《汉书新证》和《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的出版,石破天惊,轰动中外。翦伯赞先生在读完两书之后,毅然决然邀请时为讲师的陈直先生到北京大学讲学,标志着他已正式进入名师行列。我在第十届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界第二小组里与李讷相识,她当年正在北大研读历史,亲耳聆听了陈先生的讲课,一直印象深刻。在那之前,陈先生是最早将其研究成果整理成考古学教材的学者。此后还应邀去长春讲学,并与于省吾、林沄等先生探讨考古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他的努力得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的高度肯定和推举,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考古学专业早期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以上种种,是他被公推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筹备组组长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之初,会中吸引大量历史与考古两界青年才俊的决定性因素。
不过,我认为仅仅评价陈先生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似乎还不够。因为陈先生的成功,从根源上讲,主要得益于家传的古文字学。他与陈邦福、陈邦怀先生一样,从小积累了深厚的功底,这从他有关金文、陶文、简牍、封泥、玺印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上,都可以得到充分验证。比如在陈先生亲自编好的《摹庐友朋书问》里,既可与黄宾虹探讨秦汉瓦当文字和战国六国古印文字,又与王献唐品评古钱币文字;他既与郭沫若交流钟鼎文心得,还与容庚审读石刻碑拓。无论是《居延汉简研究》还是《关中秦汉陶录》,无论是《读金日札》还是《弄瓦翁古籍笺证》,无不一一显现其古文字学的识见与功力。所以,我们称他为古文字学家,一点也不为过。
总之,《陈直著作选》代表了陈先生一生研究的主要精华。它是中国学术界的宝藏,也是西北大学的骄傲与财富。希望陈门之学能在西北大学重新发扬光大,造福学子,造福学林。
陈先生千古!陈先生不朽!
(周天游,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历史博物馆原馆长)
“时代清流”刘持生先生
文|李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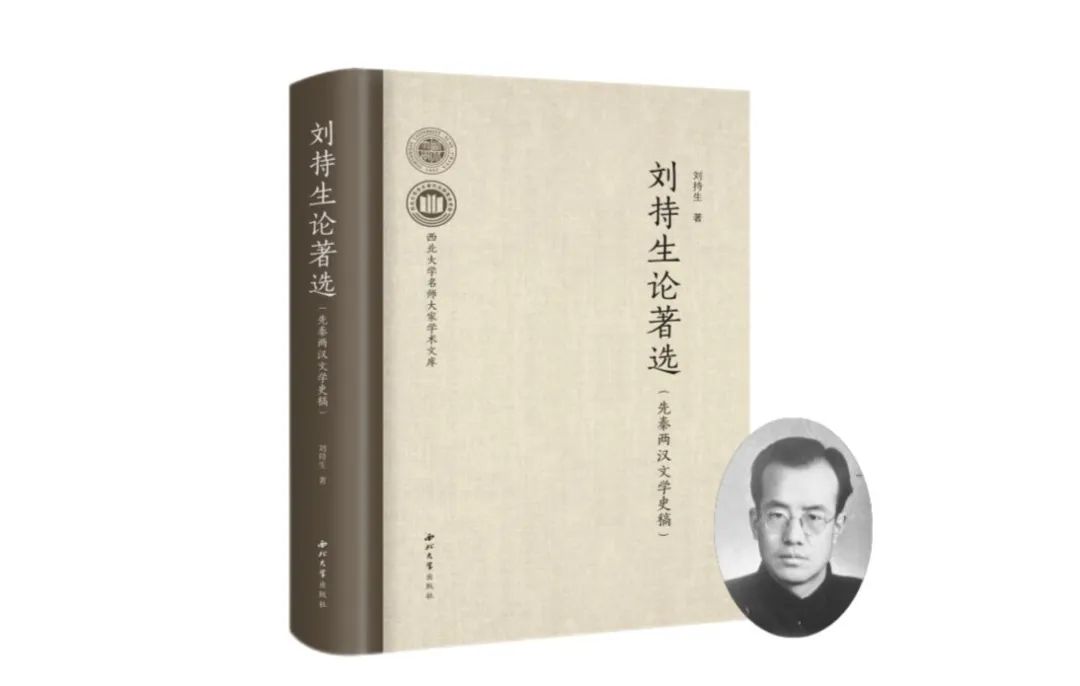
适逢西北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本着“学术校庆”“文化校庆”的宗旨,学校与出版社合作,隆重推出《西北大学名师大家学术文库》,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学术盛事。
入选本次文库的《刘持生先生论著选(先秦两汉文学史稿)》,曾由西北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初版,故这一次应该是增订再版。刘先生还有《持盦诗》一书,也是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的。与本次入编的皇皇三大巨秩《张西堂全集》相比,《刘持生先生论著选》体量不算大,但确是堪称传世的刘先生代表性学术成果。刘先生另有论文《风雅颂分类的时代意义》《陶渊明及其诗》《就“史”的特征谈北大同学新编的中国文学史》《史部目录分类商榷》等,建议再版时补入,并请刘先生的家人或学生等核校一遍。刘先生的学生在校的如董丁诚、符景垣、阎琦等学术状态都很好,他带过的研究生曹林娣、傅剑平、党保安等也很活跃。
符景垣先生曾发表过《评〈先秦两汉文学史稿〉》(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对本书有专门评价。在董丁诚先生的《紫藤园夜话》《故园情思》《紫藤园夜话续集》《紫藤园夜话三集》,赵俊贤先生的《学府流年》,姚远的校史系列著作等书中多有涉及刘先生的掌故和逸事。曹雄先生的《我的大舅刘持生先生》(《各界》2010年第3期)一文,以亲属和晚辈的身份披露了一些稀见的新史料,很有价值。2014年,我指导硕士研究生王夏琳以《刘持生与古代文学研究》为题撰写硕士论文,论文在外审和答辩过程中,受到同行专家的肯定。我受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选题和科研项目招标的启发,当时曾有一个总体的设想,就是通过硕博士论文选题,研究本学科发展史上一些知名学人。
本书第一版出来时,我就认真拜读过。印象中雷树田老师说他也参与过编辑工作,提及书稿的一些细节。我当时教《中国文学史》第一段,与刘先生此书内容的时间段近似。备课和写讲义时,经常向学生介绍刘先生的观点。除了本书,我对刘先生的两篇论文《风雅颂分类的时代意义》和《陶渊明及其诗》印象也特别深刻,每届都作为参考文献推荐给学生。
我后来随侍霍松林先生,有一次霍先生与董丁诚老师聊天,我在旁聆听。他们提及《持盦诗》中一篇作品,以及西大出版社对诗序的处理,霍先生对诗的本事做了详细介绍,我回来后将《持盦诗》与《霍松林诗词集》比较着研读了许久,确有体会。我虽然也曾拜访过刘先生,但不能算是获得亲炙,只能属于再传弟子。后来通过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不光是熟悉了相关史料,更重要的是让学脉和文化记忆通过学术书写得以传承。
我觉得刘先生除了学问一流,诗词有特色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大智慧。有三个细节可略窥一斑:其一,辞民国政府侍从室蒋介石侍从副官;其二,辞任长春大学文学院院长;其三,老先生笃信学无止境,有自己“述而不作”的坚持。这样反而能在每个时代的红火热闹处,做到激流勇退、全身保真。他仿佛能烛照洞悉一切,确有先见之明。我们许多自恃读了不少书,经了不少事的人,却总是成熟不起来,觉悟不了,每次都要在同样的地方摔跟头,看到刘先生在时代大潮中的举动,让人感慨良多。
知性的学问,纸上的知识,我们还可以慢慢地吮吸学习,历史也允许我们反复试错改正。但人生历程中,是否有大智慧,是否能力挽狂澜,是否会规避灾难,生死之门往往在一念之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总押着相同的韵脚!”刘先生擅诗词,通音律,所以能感受到历史在什么时候要押韵脚。读昔哲今贤的书,更佩服他们的特立独行,这比简单地模仿大师们的一撇一捺,一顿一挫,更令我神往。
(李浩,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治水“摆渡人”李仪祉先生
文|胡笑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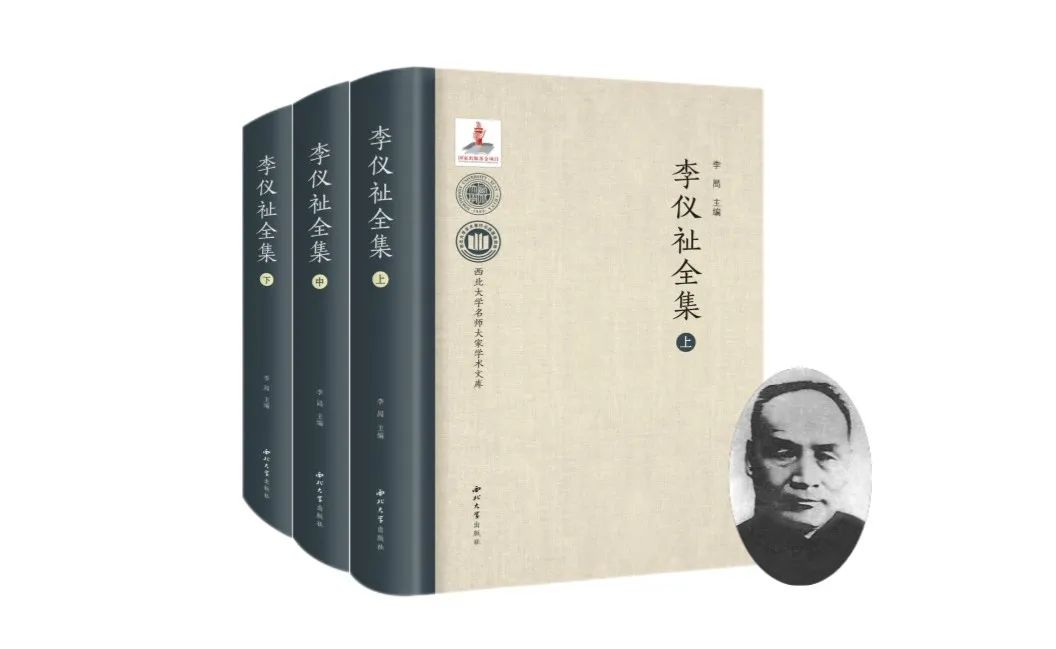
李仪祉先生1882年生于陕西蒲城,自青少年时代胸怀科学救国理想,立大禹治水之志,开现代水利先河,把毕生心血奉献给了我国的水利教育、科学及水利工程建设事业。先生自1909年京师大学堂毕业,两次赴德国留学,是我国最早学习土木与水利工程科学技术的留学生之一。李仪祉先生回国后即参与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专科学校,即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在的河海大学),并任第一任教务长。之后又创办了陕西省水利道路专门学校(后并入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水利专修班(后并入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即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专兼任多所著名大学教授,长期主持校务教务工作,呕心沥血制订学程规划,不辞辛劳亲授多门课程。
先生爱国爱民,勤学治事,一生任职70余个。创建了我国水利界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即现在中国水利学会前身,并被推举为学会会长,连任1—6届,直到逝世。每任无不竭忠尽智、殚精竭虑、功绩卓著;每事必诚有公无私、有人无我、人格高洁。
先生临危受命创建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并担任第一任委员长,首次开展黄河河道模型试验,把中国几千年来的治黄工作,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引入上中下游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新阶段,撰写的《黄河水文之研究》《关于导治黄河之意见》等40多篇治黄论著,成为后人治理黄河的纲领性文献和指南。正如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同志所说:“李仪祉先生把我国治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直到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先生情系三秦,亲拟《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亲赴陕南、陕北考察筹划汉、褒、定惠等。心连关中八惠,栉风沐雨修建泾洛渭梅,宏图夙愿终成黑泔涝沣。八惠泽被良田、河润沃土,成就了陕西关中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振兴、农民的丰足,特别是泾惠渠被誉为是开创我国现代水利工程建设的一颗明珠、一座丰碑。
先生一生足迹遍布祖国江河湖海,遍布我国17省的每一条主要江河,除了治黄、导淮、整运外,还亲自筹划了海河、长江、永定河、白河、沁河、不牢河、洞庭湖、太湖以及微山湖的整治工作,写下了许多整治江河湖泊的宏文论著,形成了完整的治河理论体系。在水利实践中,仪祉先生经过艰辛的探索,渐渐形成了丰富的水利思想,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治水兴邦、富民强国的水利思想;形成了“全面开发、综合利用”的水利规划思想,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治水思想推向一个新阶段;在水利人才培养方面,充分体现了注重实践、注重应用的水利教育思想;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水政统一、河政统一,机构精简有效的水利行政思想。
中国水利文学艺术协会(中国水利文协)副主王经国总结:“研究治水与中华文明密不可分,历史悠久,研究二者关系意义重大。李仪祉把中国传统水利思想向现代水利进行了转变,研究李仪祉水利思想就是研究中国近代水利思想。”《李仪祉全集》是李晑先生七年来搜集整理的结果,全面反映李仪祉教育、学术、咨政及治水思想。在李仪祉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西北大学出版社推出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总结和传承李仪祉水利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胡笑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院长)
资料转载:西北大学出版社